

CSD 2025微专辑
扫描二维码
可查看更多内容
仲夏

苏飞教授
你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直接点到了问题的核心。组织细胞增生症的确是一组罕见疾病,它的狡猾之处在于,它非常善于“伪装”。很多时候,这类疾病的首发表现,甚至唯一症状,就是皮肤损害,而且这些
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儿童的
所以,我们皮肤科医生其实是站在了诊断这类疾病的“最前线”,扮演着“预警机”的角色。患者因为皮疹最先找到我们,我们是第一个有机会揭开它们伪装的人。如果我们对这类疾病缺乏警惕性,诊断就可能被延迟,患者可能会在多个科室间长期辗转,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对于一些侵袭性的组织细胞增生症,比如累及“风险器官”的LCH,这种延迟可能是致命的。因此,了解它,不是为了处理多少罕见病,而是为了在我们日常大量的“常见病”中,能敏锐地识别出那些不寻常的“冰山一角”,这对改善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

当然。过去的分类比较混杂,但随着我们对疾病本质认识的深入,分类体系也越来越清晰和实用。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是基于2016年国际组织细胞学会修订、并被后续WHO分类采纳的框架。这个框架非常巧妙地将上百种复杂的亚型,归纳为五个大的组别,分别用五个字母命名:L、C、R、M、H。
L组(Langerhans-related):这是朗格汉斯相关组,核心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和Erdheim-Chester Disease(ECD)。它们虽然细胞形态不同,但因为共享了关键的发病机制而被归为一类,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C组(Cutaneous and mucocutaneous):这是皮肤和黏膜组,主要指那些几乎只累及皮肤和黏膜的非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幼年性黄色肉芽肿(JXG)。
R组(Rosai-Dorfman disease):这一组的核心就是Rosai-Dorfman病(RDD),一种以巨大淋巴结肿大和特征性病理表现为主的疾病。
M组(Malignant histiocytoses):这是
H组(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和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组本质上是严重的免疫失调和过度炎症,其组织细胞浸润是反应性的,而非肿瘤性增殖。
这个分类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再仅仅依赖于细胞长什么样,而是整合了分子遗传学、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更能反映疾病的内在联系,对我们的临床诊断和治疗选择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苏飞 教授
问到点子上了。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组织细胞增生症领域最重大的认知革命——即从“反应性/炎性疾病”到“肿瘤性疾病”的范式转变。过去我们认为LCH等疾病可能是对某种未知刺激(比如病毒感染)的过度炎症反应,但现在我们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是源于骨髓中单个祖细胞的克隆性增生,也就是一种骨髓源性的肿瘤。
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就是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的发现。你可以把MAPK通路(具体就是RAS-RAF-MEK-ERK这条级联通路)想象成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油门”。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油门”是受严格调控的,需要外界信号(如生长因子)来踩一下,它才会启动。但在绝大多数LCH、ECD以及部分RDD和JXG患者的病变细胞中,我们都发现这个通路的“油门”被卡住了,处于持续“踩下”的状态。
导致“油门”卡住的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通路的关键基因上发生了体细胞突变。其中,最著名的“明星突变”就是BRAF基因的V600E位点突变,它存在于大约一半以上的LCH和ECD病例中。此外,还有MAP2K1、ARAF、KRAS等其他通路成员的突变。
这个发现的意义是颠覆性的。首先,它为这些疾病的“肿瘤性”验明正身。其次,它像一条主线,将LCH、ECD这些过去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疾病,在分子层面串联了起来,揭示了它们共同的致病核心。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临床上会看到LCH和ECD同时出现在一个病人身上的“混合性”病例——因为它们可能源于同一个携带了MAPK突变的骨髓祖细胞,只是在不同组织微环境下分化成了不同的样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直接催生了精准治疗的革命。既然“油门”卡住了,我们就可以开发专门的药物去松开它,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的BRAF抑制剂和MEK抑制剂。

苏飞 教授
我们皮肤科医生在L组疾病的诊疗链条中,地位非常独特且关键。优势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我们是“第一目击者”。L组疾病的皮肤受累率非常高,比如LCH,有40%到80%的患者会有皮损,而且常常是首发症状。这意味着,在患者自己和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还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疾病最原始、最直接的线索。
第二,我们掌握着“关键钥匙”。这把钥匙就是皮肤活检。皮肤活检相对其他器官的活检来说,操作简便、创伤小、安全性高。对于一个可疑的皮损,我们能非常方便地获取组织样本,交由皮肤病理医生进行确诊。可以说,没有病理,就没有诊断。而我们皮肤科医生,正是连接临床表现和病理诊断之间最直接、最便捷的桥梁。
但优势也伴随着责任和挑战。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一定要敢于怀疑,勇于活检。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典型的、治疗抵抗的“湿疹”,一个不典型的黄色丘疹,或者一个婴儿头皮上反复不愈的“脂溢性皮炎”时,脑子里一定要多一根弦,想到“会不会是组织细胞增生症?”。一旦有了怀疑,就不要犹豫,取一块皮损送病理。在申请病理时,最好和皮肤病理医生充分沟通,告诉他们你的临床怀疑,这样可以引导他们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观察和选择免疫组化染色,避免漏诊。我们的一个小小举动,可能就为患者赢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宝贵时间。

苏飞教授
很好的问题,这个模型是理解LCH乃至L组疾病临床异质性的核心理论。所谓“髓系分化误导模型”(Misguided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Model),它描绘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疾病发生画卷。
这个模型告诉我们,LCH的病根,并不在皮肤。致病的基因突变(比如BRAF V600E),最早是发生在骨髓中的一个非常早期的造血干细胞或髓系祖细胞身上。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应该分化为成熟的、发挥正常免疫功能的细胞。但MAPK通路的“油门”被卡住了,处于持续“踩下”的状态。它们的分化和增殖就失控了,最终变成我们病理上看到的、病理性的CD1a+/Langerin+的LCH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招募大量的炎性细胞,形成我们临床上看到的皮损或骨破坏。
这个模型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它完美地解释了LCH为什么临床表现千差万别。
如果突变发生在非常早期的、能到处跑的多能干细胞里,那么它就可能播散到全身,导致侵袭性的多系统疾病(MS-LCH)。
如果突变发生在一个比较晚期的、已经“安家落户”在某个组织(比如骨骼或皮肤)的定向祖细胞里,那么它就只会在局部“作乱”,导致局限性的单系统疾病(SS-LCH)。
这个模型对我们理解所有组织细胞增生症都有启发。它告诉我们,这些疾病本质上是“一个根(骨髓起源的克隆突变),开出多样的花(突变时机影响临床表型)”。
审核专家:苏飞教授
专家简介
-苏飞 教授-
武汉市第一医院
博士,副主任医师
美国南卡罗莱纳医科大学皮肤病理国际访问学者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病理学组成员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皮肤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病理学组、甲病学组、皮肤肿瘤学组、远程医疗及人工智能学组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皮肤医学分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皮肤肿瘤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委员会委员
中国罕见病联盟/北京罕见病诊疗与保障学会皮肤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擅长特应性皮炎、银屑病及疑难罕见疾病的诊疗,皮肤病理诊断及美容激光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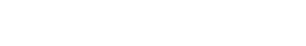
医脉通是专业的在线医生平台,“感知世界医学脉搏,助力中国临床决策”是平台的使命。医脉通旗下拥有「临床指南」「用药参考」「医学文献王」「医知源」「e研通」「e脉播」等系列产品,全面满足医学工作者临床决策、获取新知及提升科研效率等方面的需求。

(本网站所有内容,凡注明来源为“医脉通”,版权均归医脉通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医脉通”。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转载仅作观点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版权,请及时联系我们。)